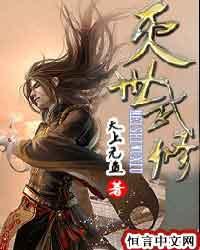逆天換明第四百零一章 九州之鐵難鑄其錯
站在城牆上,舉目瞭望,還能看到士兵在城外種植的田地,主要是已經綠油油的蔬菜。
但在祖大壽看來,這裏已經象一座牢籠,困住了他和三萬左右的官兵。
輕輕拍着城牆,祖大壽沉聲問道:「朝廷命我軍屯田耕種,從今年秋收後,餉糧便要減少四分之一。」
當時給遼鎮士兵的餉糧是每月一兩四分銀和一斛米,而東江鎮的軍餉則是七分銀,只有遼鎮的一半。
現在,東江鎮官兵的餉糧已經與遼鎮一樣,遼鎮則要在數月後面臨減糧的困難。
在祖大壽看來,不是朝廷錢糧供應不上,減糧更象是一種懲罰,懲罰他們背叛朝廷的私自竄逃。
謝尚政的臉上浮起陰霾,緩緩說道:「減少四分之一的話,倒還能支撐過去。只怕明年再減,後年再減,直到完全斷絕供應。」
「朝廷要把我們逼入絕地。」祖大樂哼了一聲,說道:「這是鈍刀子割肉,慢慢地收拾咱們。」
祖大壽的目光閃了一下,說道:「某已上奏朝廷,寧遠地瘠田少,即便屯田耕種,一年也不過萬石。何況,我軍移防寧遠,農時已過,今年已難種糧。」
停頓了一下,他又補充道:「況且,寧遠乃關門唯一屏障,為建虜必攻之地,屯田訓練恐難兩全。」
忽悠,接着忽悠。別說建虜今年已經喪失了進攻的物資基礎,就是有,恐怕也不會頭鐵到再來寧遠城下挨炮轟。
如果建虜恢復了實力,倒是可能再行繞道入關。當然,有東江軍牽制着,建虜也很難再重施故伎。
「風水輪流轉哪!」何可綱重重地嘆了口氣,說道:「現在是東江鎮得勢,咱們已經不被朝廷看重了。」
說到東江鎮,眾將表情不一,有忿忿的,有皺眉的,有黯然不語的,表現出各自的心情。
祖大壽也嘆了口氣,說道:「沒想到,東江鎮發展壯大得如此令人震驚。能以相差不多的兵力,硬抗建虜猛攻,並能反擊獲勝,我軍自問是難以做到的。」
遵化大捷的詳情,祖大壽等人已經知曉,用震驚已經不足以形容他們的心情。
儘管這幾年東江鎮確實屢獲勝績,但慣性思維卻使他們想出各種理由來貶低篾視,並不願意承認東江軍戰力的快速提升。
在他們看來,缺糧少餉的東江鎮,只能夠襲擾牽制建虜的叫化子軍,竟然在短時間內便是近乎脫胎換骨般的變化,實在是難以置信,不可思議。
不僅是他們,袁崇煥在位的時候,也絕不相信在他百般壓制和封鎖下的東江軍,能有如此飛躍式的發展。
也正因為這種心理的慣性,祖大壽才做出了擅自脫離戰場,返回遼西的決定。
一來是袁崇煥被下獄,他確實怕了;其次則還以為大明缺了他們「關寧鐵騎」不行,會哭着求他們回去。
自大和誤判終於導致了目前的局面,祖大壽等人很後悔,可反過來再想,在京城之下與建虜死戰,結局也不見得好。
「東江鎮能夠挺過缺糧少餉的困難時期,不過是倚靠水師,對外貿易來獲取物資。」謝尚政沉吟着說道:「我們有覺華水師在手,善加利用,難道就能坐困愁城?」
何可綱搖頭道:「從外購糧的話,需要多少錢財?縱是能撐得一時,終不是長久之計。」
「既是貿易,自然要有賺頭。」謝尚政說道:「難道東江鎮就只出不進,他們又哪來的那麼多錢財?」
祖大樂說道:「聽說東江鎮做的是走私貿易,從建虜手中換得參貂鹿茸等物,賣到江南便是數倍的暴利。」
祖大壽的目光一閃,心中有了個主意,緩緩說道:「這倒是個辦法,可卻需從長計議,現在就不必討論了。」
走私是個好辦法,東江鎮能做,我們為何不能?只不過,讓太多人知道可不好,祖大壽準備只找幾個心腹做這件事情。